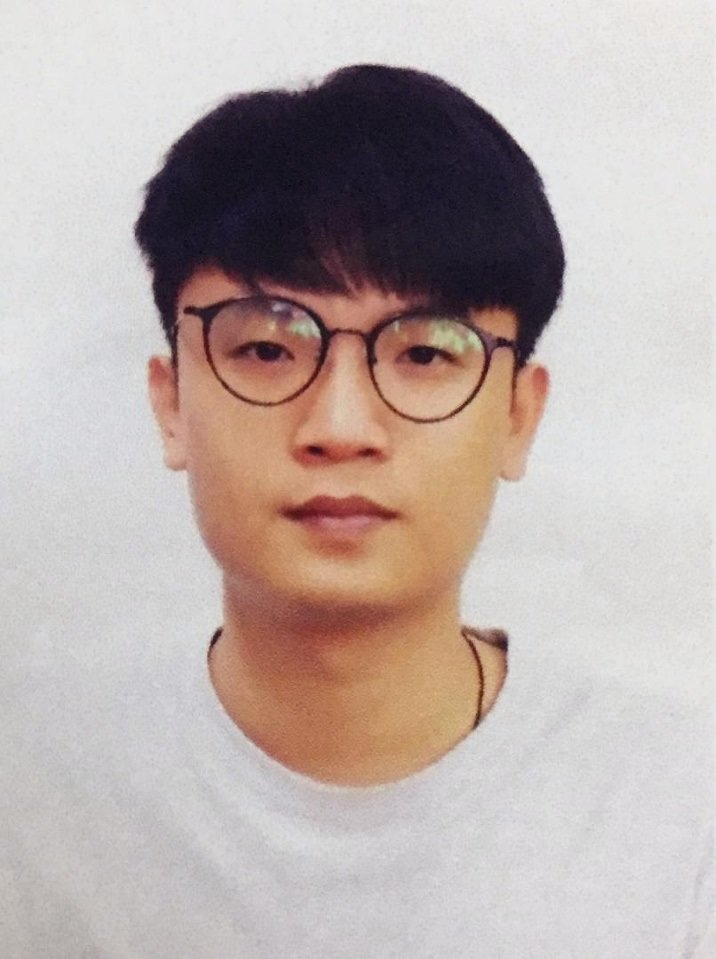2025年2月1日,大年初四,托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之名,在槟城庙会支起传拓体验摊子。或因此,竟无意回返J,反倒大年初一匆匆回森美兰过年,初三复又折返槟城。这途中生了场大病,不知是风寒入骨,还是俗称的“发热气”,只觉浑身沉重,恍若被岁月碾过。然而槟城庙会人潮汹涌,不敢怠慢,遂吞药拎器,拖著病恹恹的身子,硬挤入翻涌的人流。
活动开始,果然“人潮汹涌”。幸而庙会负责人早有安排,调配人手相助,一切尚能应付,不至手忙脚乱。在此,尤要感谢 Lesteric 及四位志工,虽不知其名,却见他们奔走张罗,或维持秩序,或解答疑问,忙得汗流浃背,仍不辞劳苦。他们的用心,令人动容。若非如此,这摊子怕是难以支撑至深夜,而我也未必撑得下来。
然而,要在短短几分钟内学会传拓的基本功夫,简直是天方夜谭。传拓何其繁琐,三言两语恐难以掌握。为应对眼前局面,只得省却繁琐细节,让志工迅速上手,也让参与者免于因复杂流程而失去兴趣。否则,哪有那么多时间慢慢叙述?毕竟,在这里,时间是奢侈品。鲁迅先生曾言:“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空耗他人时间,实则谋财害命。”
关于那些省略后的结果,我想,倒是有些可记的价值。譬如,只拓那印模上的小纹饰和小文字;又如,用那便宜的纸张与墨汁,代替本应昂贵的材料;再如,那纸张不待自然风干,便以纸巾粗暴吸去水分。每一步的妥协,仿佛是无法逃避的宿命。明知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然而又能如何?这些省略与调整,终究不过是无可奈何的退步,实在是为了速成而付出的牺牲罢了。
至于“人潮汹涌”般的参与者,我原以为愿意驻足聆听的,大约是些鬓发斑白的老人,或是眉头紧锁的青年,心中装著千百个疑问,带著几分寻幽探密的意味。谁知,最专注的竟是那些咿呀学语的孩子。他们挤在最前头,睁著亮晶晶的眼睛,听得入了神,甚至连衣角被人拉扯了,也全然不觉。有人小心翼翼地触摸那拓片的纹理,有人睁大眼睛盯著墨色晕开的瞬间,仿佛窥见了什么珍贵的秘密。
望著他们,我不禁心生感慨。这些孩子,如今尚能为这些看似不足挂齿的事物驻足,哪怕只是出于一时的新鲜。可这份新鲜,未尝不是一粒种子,埋在心里,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愿他们日后,面对国外学者质问这些文献该如何收藏、如何保护时,也能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们的文献,自有我们护持。传拓,我们也同样稳当。”那时,今日这短短的一瞬,便不只是好奇的停留,而是一道烙印,一种信念。
眼下,我们的功夫、财力、条件,自然难与国外相较。倘若比拼设备的精良、技艺的纯熟、体系的完备,我们恐怕是望尘莫及。然而,路总要一步步走,事总要一点点做,只要肯持续耕耘,发挥自身的特色,自然能闯出一条生路,甚至走出一条旁人未曾踏足的路。
譬如室内传拓,我们固然远逊于两岸三地,技法不及,设备不及,连器材也不及,终究难以与那些积累深厚的地方相提并论。这是事实,无须讳言。但户外传拓呢?马来西亚的烈日、骤雨、湿气、风尘,这些旁人避之不及的桎梏,未尝不能成为磨砺技艺的砥石。困境是有的,难处是实的,可只要下得苦功,肯总结,敢尝试,愿琢磨,总能摸索出一套适合本地条件的方法,进而磨出自己的锋刃。待到将来,若有外国学者问起,我们不必唯唯诺诺,也无须低声下气,便只管挺起胸膛,说一句:“室内,我们或许不如你们,但户外,尤其是在马来西亚,我们自有我们的法子。”那时,今日所植下的种子,便已扎根破土,纵使风雨如鞭,也拦不住它破土抽芽。
行文至此,忽然忆起多年前,在 S 大学学院听 A 老师讲过的一段故事。据说当年 S 还只是个学院时,马来学系的陈育青讲师曾说:“马来学系的儿女,是造桥的人。我们要来造一座文化之桥。”此言铿锵,至今犹在耳畔。
桥是什么?桥是沟通,是连接,是在江河断岸之间搭起一条生路。古人造桥,是为了让行人能渡水,免得被激流吞没。如今的造桥,却是为了让文化能通行,免得在时代的风浪里沉没。文化失了传承,便如断桥残梁,纵有旧迹可考,也不过是荒草封锁的废墟罢了。
我们这一代人,技艺不及前人,学问不及大师,手上所握的,不过是一点薄技小艺,撑不起什么惊天动地的桥梁。但世间许多桥,原也不是一夜筑成的,先人凿山引路,后人铺石架梁,终有一天,能叫人安稳行走。传拓这门手艺,若只锁在书册里,束之高阁,终究只是死物;只有传开去,拓下去,哪怕只是教会一个人,多做一方印,便也算是架起了一块踏脚石。
造桥的人,并不问桥何时成,也不问自己能不能走过去,只知一步一步,把眼前的石头安放妥当。这桥,哪怕只通一人,也总好过任其湮灭。
2025年2月5日 大病
吉礁莒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