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导@张溦紟
江琼珠:拍一部社运文艺片
“我们在此相遇”纪录片,由香港资深记者兼纪录片导演江琼珠 + 拍摄,日前已分别在吉隆坡、怡保、槟城、新山等地首映。去年,江琼珠就带著“几乎是革命”、“我们总是读西西”等纪录片来马与观众交流。她讶于马来西亚观众对于香港社会发展之关切,公开许诺若有下一部纪录片,一定来马来西亚播首映。果然,这次她按照约定来马,带著临上机前才剪辑完毕的纪录片。
在拍完纪录雨伞运动的“几乎是革命”之后,身心疲累的她不想再跟著示威群众跑来跑去,心想拍一部社运文艺片吧。毕竟,传统社会运动多偏向集体和公共,谈论述战略,鲜少谈自己,于是从社运行动者的生命轨迹出发,看见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异同。

这部纪录片记录香港和马来西亚五位社会运动行动者与社会运动的相遇,他们分别来自港马的五位行动者跨越不同世代和社会,他们包括:区美宝(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图1)、李凯伦(公正党马章武莫州议员,图2)、张永新(文运出版社,图3)、陈允中(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图4),以及刘嘉美(自由撰稿人,图5)。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整理部分受访者的经历,如何随著不同的人生际遇、生命阶段,在不同城市和事物的变幻,面临抉择而自我调整或偏执坚持。
陈允中:守护不想放弃的人
陈允中,砂劳越诗巫人,17岁只身到台湾求学,原本是个爱国的乖学生,一旦听见某处奏起国歌就会笔挺站立,即使那里空无一人。有次新年寒假回马,当时留学台大机械系的陈允中亲眼看见52名原住民,因抗议家园被破坏而遭警方逮捕。他们一个个依序从警车走下,身上套著手铐脚镣,处境像动物一样卑微。他回忆起这段社运启蒙的过往,忍不住哽咽:

他追到法庭,也不管可否拍照,像记者一样,记录眼前这般荒谬暴力的现实。当时尚未是社运组织者的他,拿著一堆资料准备和最亲近的、也是读书人的家人商量对策,却被质问是否被人洗脑。他指著可作为证据的纪录片DVD,要求家人看了再说却被拒,于是把自己关在房门里,不过年、不洗澡、不吃饭,想用自己的方式与无辜被捕的原住民共进退。

眼前这一幕当然急坏了家人,因为我们的外在世界总是那样“正常”。最后,主动同意陪他看完整一套纪录片的,竟然是全家唯一识字不多的婆婆。经历过那一次“家中小革命”后,对家人和他自己都是一次洗礼。
作为社运组织者,经常需要说服大量陌生人,关心和支持边缘社会议题,但是偏偏要说服生命中最亲近的家人,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累积更多组织经验,他慢慢理解,原来要改变一个人根深蒂固的“偏见”是异常困难的,需极大耐心;加上后来学佛,他才开始释怀,家是一个你要感恩的地方,从此对家人的政治要求归零。
经历台湾解严后的民主化运动——三月学运、妇女新知、原住民正名运动、无蜗牛运动,他与台大城乡所的伙伴从此踏上了社运之路。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书,继续参与在地社区运动,近年参与保卫皇后码头、菜园村抗争、反高铁、占中等,长期蹲点与基层站在一起。
身在海外三十馀年,某个意义上,他从未真正回马,对于回不回家,如何回家,始终是他多年反复思量的命题。作为一个耕耘社区,抵抗社会不公的社运行动者,怎么可能背向同样需要人蹲点的家乡呢?
他每年趁假期回家数次,除了陪伴家人过过日常生活,就是到处去拜访非政府组织,然后带著60公斤厚重的相关资料回台港啃读,为某种缺席努力补课。约22岁那年,他下定决心终生以社会运动为志,更自我期许为“国际在地主义者” + ,哪里有不公不义、哪里可参与改革的,就是他的“家”。未受主流以国家边界、国籍身份或血缘出生地所定义的“家”所限。
刘嘉美:好想回到基层
刘嘉美,自由撰稿人,也是纪录片受访人之一。听过她名字的人,大概都可在示威游行、网络或平面媒体专栏,或是电视新闻节目见过她的身影。可是,书写评论却不是她最理想的位置。
早在大学念书时已积极参与社会,走在社运前头。影片中回溯至2006年,她参加香港七一大游行,站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呼吁大家正视清洁工人权益。搬来马前,她身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从事劳工组织工作。

来马后,她从未刻意串联港马之间的社运组织,但总会碰到这些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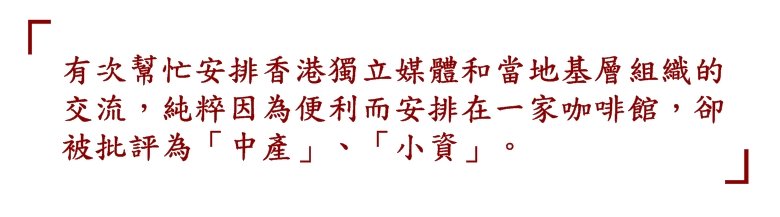
在基层运动里,被标签为“中产、小资”,意味著你对阶级意识尚未觉醒。出身基层家庭的她非常介意这个称号。对她而言,在意的不是别人的批评,而是你处于什么阶级位置,会影响了你的视角和观察,是否还能跟基层感同身受。
就像她一开始对撰写专栏文章,上电视评论时事的位置感到很不舒服。相对于基层组织,她认为书写和评论位置,始终是一个有距离的旁观者,而非与苦主同在,“好想早点返去基层”,一语道破她心中所系的自我定位。
碍于马来西亚政府对外籍配偶的严苛管制,她不能自由地从事理想的工作。不甘心的她经常拿著电脑搭公共交通穿山过省,与各地社运组织交流或出席活动,想要借此贴近土地。也因为经常移动,她对于变动中的视角和位置也有所醒觉。
作为一个女性行动者,除了要跟大家一起对抗社会制度的不公,她们同时还要松绑种种社会对于关于性别的规范和枷锁。
“我不会说我嫁来马来西亚,而是说我搬来这里”。她在影片中受访时,正在香港出席大学社工系同学的婚礼,强调婚姻不是她人生的选项。大家有一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思维,就连不舍得她离开的原生父母也认为,她应该跟随丈夫同时也是李凯伦到马来西亚生活。
“可是,不会有人倒过来问李凯伦,你要不要到香港去和刘嘉美一起生活”。她直言这样的思维对女性很不公平。
张老板搞出版,继续靠左
大家私底下都习惯称张永新为“Pak Chong”或“张老板”。1960年代,左翼风潮遍布马来西亚、东南亚甚至印度支那,张永新积极参与左翼运动,被关进扣留营长达8年1个月。中学未毕业的他,却在三个扣留营陆续遇见许多大学生、律师等知识分子,密集大量的学习各种知识。1970年代中,重返社会后,花了好些时间重新适应社会的步调,却从未放弃社会改革,继续参与人民党创立;一直到2000年,人民党遇到很大的阻力,才下定决心转型,投入文化运动,搞出版社。

他第一次接受江导演采访时是2007年,当时还是在出版社旧址。文运出版社刚开始只有两三人,出版刊物涵括左翼历史和理论、社会科学、政治、文化和经济等。他回想搞出版社的初衷,“思想不改变,政治如何改变?我不敢说没有人做(出版社),但是我真的是没有看到有人在做。这不是纯生意,不是纯出版,不是卖书那么简单而已,还要办活动、讲座,与社会和年轻人结合。这些都是不赚钱的,要贴钱的,可是这样才有意思。”
“我常说,那些没有人出版的书,我们出;那些不赚钱的书,我们来做,只要我们能够存活。这样才有挑战性。没有挑战性的事情,你做来做什么?这样才刺激,才有意思。”

江琼珠早在一场研讨会见过出版左翼书籍的老板张永新,更在2013年出过一个关于他的纪录片“张先生搞出版,持续靠左”,却一直不满意拍摄成果,只见文运出版社近年又有一些进展,不惜自费跟拍再次出现于“我们在此相遇”纪录片中。
再次拿起摄影机拍摄张永新时是在印尼日惹,是一个关于重构马来亚史的学术研讨会。相对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金融经济蓬勃发展,印尼日惹是一座文化城市,集合多所大学、出版社、书店。他抓紧机会跟当地出版社联络,商讨是否可能合办一个“小而特殊”的书店,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区域连结”。他常说“我是群岛人”(Orang Nusantara),要如何在连结泰菲印越新马,建立文化基地,进行思想传播,促成青年交流,是他长期的梦想。
“我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年轻人。......我现在情绪高涨、兴致勃勃、充满活力。.......做这些事情,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伟大咯,不需要这么谦虚的......”话一落,连张永新本人也忍不住大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
每次张永新的画面出现时,总是引起现场一阵大笑。江琼珠导演说她并无意将他拍得那么搞笑,但是不知为何总会有制造这种意外的“笑果”。她偶尔会调侃他的“臭屁”,却正面补抓这位社运行动者自我肯定的一面。从她多部社运纪录片中,处处可见江琼珠诚实地记录社会运动的起起落落,这些社会运动者有激情、期待、希望,却又在一瞬间掉入谷底、低潮、迷惘。

面对主流社会种种高墙的镇压、质疑和否定,偶尔微弱偶尔强大的社运在时间长河里绵延,站在对立面的鸡蛋们,谁还能那么肯定自己要走的路。她说,“他们不会放弃的”。他们不管身在何处,都不会放弃的,过去不会,现在不会,未来也不会。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是多年来记录社运行动者告诉她的事。
-
江琼珠,资深媒体人,纪录片导演。
小学毕业在玩具厂做过暑期工;1970年代跟大学同学到工厂区派传单反对巴士涨价;曾住进巴芬道公社过集体生活;1980年代加入记者行列,在主流媒体打游击战,从撰写社会边缘小人物开始,从街边阿婶、拾荒阿婆到电子成衣厂女工,写多少是多少。
1997年,香港回归,毅然办“进一步”出版社,寻找和社会的关系,出版百多本社会科学等书籍;同时,接受非营利机构的委托,写了大量老人护理、病人、农夫、中国维权律师的故事,也不管书卖不卖,看的人多不多。
2004年开始拿起摄影机,用影像记录社会运动。后来,她对出版社前景不甚乐观,一两年前从出版社退下。不过,她仍然不断书写,就像她从不停歇地拿著摄影机纪录社会运动一样。
她的纪录片从不强调主流的客观独立,第一部纪录片“姊姊妹妹与紫藤”,说的是性工作者和相关组织的日常故事,随后展开社会运动系列四部曲,在2005年拍摄反世贸期间,更一度从一位记录者意外转为绝食者。
做事一向迅速利落的她,倒是对于做文字工作或纪录片的影响力有出奇的耐心。她用影像和文字纪录属于自己那个时代的社运故事,用前曙光书店老板马国明的话,“为的是留给下一代一个明白的机会”。她曾在文里说,“不明白是正常的,重要是我们有多少空间和耐性让自己明白”。她的纪录片不烧成DVD,也不放在网络公开流传,侧重与观众的现场交流。她宁可四处放映,为的就是“在静水中掷下一颗小石子”。
- 国际在地主义主张破除僵化的国家边界和国族想象,从阶级、性别、少数族群的位置,从眼前令人困扰的现象和问题来介入现实世界,来重构在地的论述、经验和知识。



